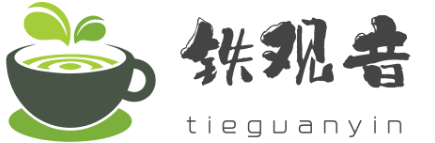采茶,采茶文章

近来,读到唐代文学家徐寅诗里的句子:“武夷春暖月初圆,采摘新芽献地仙。”蓦地想起20年前,在江南茶场附近居住的生活。徐寅写的是武夷山的茶,我熟悉的是江南吴下琴川虞城三峰山的茶。
虞城自古就有“十里青山半入城”之称。这半入城的山并不高,但入眼便是干净起伏的青翠。有山,就应该有茶,茶树在青山起伏的怀抱里。山和茶相伴,就像人和友相随。山是茶的依傍,茶是山的知己。虞城最早种植茶树始于清代,据《常昭合志》卷十五物产志记载:“茶,绿色,虞山间有之,名本山茶”。就是说虞城的茶树始于虞山。品种以碧螺春为主。清明前采摘制作成茶,名为毫,清明后采摘制作成茶,名为炒青。其茗毫、毫峰更是名闻天下。
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最神奇的树叶,就是茶叶。小小的一片叶子,溶了水,浸入色,凝出泽,飘发香气,散尽叶片的精髓。且不说令人提神醒脑精力充沛增加免疫力,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的佳章好文,都是靠忙里偷闲一杯茶或静坐思道的这杯茶,生发出来的灵感等等;就是百姓民生,来人待客人情往来,都靠一份茶礼,来彰显自己的品味,和对客人的尊重。
初到虞城,我便因为对茶树的久仰,租住在三峰茶场对面的民居。
因此我发现,每年清明节前的那几天,天色刚放出微光,虞城204国道旁边的茶园,还沉浸在酣睡的宁静里,就被成群结队的,往茶山上涌去采茶的人流打破。人群里大多数是头裹花花绿绿的头巾,操着本地方言,叽叽喳喳的阿姨们。阿姨们的声音很有特点,也许是当地方言的发音习惯,她们说话的语速很快;又也许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妙处,虞城的阿姨们无论多大年纪,无论外形和年轻两个字相差多远,从她们喉咙里吐出的声音,普遍尖细嘹亮,似乎都天生就有女高音的禀赋。常年的劳动也使得她们的肺活量发达,发出的声音底气充足,共鸣悠远。所以如果一群阿姨们在一起,用方言聊天,就是哒哒哒哒一群小马达,外地人听起来像是吵群架。
立春伊始,春分过后,清明之前的清晨,吵群架的喧嚣又开始每天从我窗前掠过。其中夹杂了少数时不时用浑浊的乡音大叔们的烟嗓,和中年人疲倦不甘的哈欠声。透窗细看,去采茶的人们,一般都有个明显的标配,系上一条或新或旧或花或素,但长度必须过膝的围裙。此时的江南早已经春暖花开燕归鸟鸣,天并不冷,为什么要系围裙,还那么长?远看像苏格兰裙子似的,我一开始没琢磨明白。
茶场对去采茶的人,没有明确的规定。男女老少年轻年老本地人外地客,会不会方言有没有文化是否喝茶,一概不论谁去都行。但是茶场在茶山的坡下顺势盖了一排储存、称重、算账的房子,围挡了不允许随便进出的铁艺墙,有固定的给采茶人进出的门。这就意味着,采茶的人们进来可以,但出去的时候,必须要通过称茶的地方,把采到的茶叶拿出来。茶场工作人员会对茶叶进行称重,辨别成色品级,再算工钱。如此一番操作完成,采茶的人才能走出茶场。
我这个家乡没有茶园的北方人,有一次心血来潮,特意在单位请了一天的假。一大早,从听见阿姨们的第一声笑语,就爬起来跟着人流去茶场采茶。因为没有围裙和头巾两大装备,两腮也没有因为户外劳作,被长年累月火辣的太阳,晒出些许红血丝的酱色。茶场门口坐在木椅子上把门的阿姨,只抬眼瞄了我一下,便用方言式普通话问:“你是第一次来?”
我挠了头皮心虚地点头,不免忐忑,生怕被把门的阿姨看出我凑趣儿的心理,剥夺了我这次以玩为主,以干活为辅的实践趣事的机会。不过,阿姨把头一偏,示意我从架子上拿块头巾带上。头巾是农村集市常见售卖的,娇艳的大粉色和大蓝色、白色交错成格子图案的针织方巾,新的时候必定是色彩绚丽十分醒目。但是已经旧了,大粉和大蓝色彩都褪色的深浅不均,我并没有戴头巾的习惯,尤其这种不好看的头巾。但是在把门阿姨盯着我毫不通融的目光当中,我权当这是进场的必备程序,就像有的单位打卡进门之后,必须要戴工作帽一样。虽然之前没有戴过,但我有样学样的能力还不差,一边把整个脑袋上半截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一边踩着前面阿姨们的步伐走到茶树垄里转。
按照采茶业大家心知肚明的行规,已经有了人的茶树垄,是不能停留的。我又是学习观摩阶段,一路走走看看,等我找到空茶树垄的时候,已经到了山坡上,转头看离大门快一里路远了。坡上风大,太阳也开始初露热芒,这时我才明白,老阿姨们都带着头巾的道理,那勒令我带头巾的把门阿姨,立刻令我心生感激。
清明节前,正是采摘茶树最顶端嫩芽,即毛尖的时机。
碧螺春的嫩芽,一般都是一芽一叶或二芽一叶。它们挺着娇黄带绿的身姿,娇小纤细的只有一个指甲的长度,在晨风中,羞答答颤巍巍地,端坐在茶树枝丫的最顶端,俏嫩羞涩的,像刚到及笄之年的小姑娘。
“就是这个叶尖头,尖芽子哩!”路过的一个阿姨见我懵愣地傻站着,顺口指点我。
但是这“小姑娘”已然令我爱不释眼,手指触摸上去,叶片光滑柔软,竟不舍得摘掉。面对行垄里,一棵棵翠绿繁茂,高度及胸腰部位的茶树,我完全不知道从哪片柔嫩的小叶芽儿下手。大自然用日月风华赐予世间如此妙物,人一出现,为什么就要把它们从天然的原生态,转移到自家的客厅厨房,乃至杯中呢?转念我又想,如果人们不把它转移到杯中,又岂知它的妙处,它又怎会有图腾般的文化价值。况且,如果我这时候不把它采摘,不出十天,它在枝头就老了,它的青春就无人赏识。
我用人类的虚伪和理论,安慰了自己一番之后,便开始摘树芽儿,往往一棵茶树采不到几枚嫩芽。脚步随着眼睛的探索,手的动作不停挪移,不一会,胸腹及大腿的衣料便沾染了露水的湿气,凉丝丝的贴在身上。此时我才恍然大悟,采茶的人们都系个长围裙的妙处。一条茶垄下来,我数了数塑料袋里的嫩芽,有几十片。一份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但是,当我的目光,扫向前面阿姨的塑料袋时,刚升起的这点小欢喜,立马荡然无存。前垄两位阿姨的袋子,已经鼓鼓囊囊,装了大半袋黄绿色的茶叶芽。而此时,她们褶皱枯瘦的手指,仍旧围着茶树上下翻飞。动作灵巧得仿佛是在树丛里,穿针引线的绣娘。而她们原本干瘪枯黄的脸,也瞬间生发出,如年轻女子一般的光华和灵气。
我在她们身边瞅了一会,深深叹服阿姨们,把柳公熟能生巧的理论,落实的完美无缺。
到中午,采茶的人群开始下山称重的时候,我塑料袋里的毫尖,竟然不到二两。
“这么一点点——”称重的阿姨正是早晨督促我戴头巾的阿姨。
我摘下头巾老老实实地挂在原处,尴尬地小声嘟哝:“阿姨你看我摘的这嫩芽芽儿,太嫩了不占分量。”
“这么一点点不好算账,你干脆自己出钱,把茶叶买走回去喝。”阿姨给我指了一条明路,也满足了我没敢奢望的想法。
摘下来的新茶,下一步就是炒茶。
虞城地处长江下游,水分多湿度大晴天少。所以炒茶之前,得祈祷有几个晴天。先把新茶用清水冲去灰尘虫卵之类的杂质,再均匀摊在日常生活用的竹簸箕上,放在日光下晒上两天,蒸发干新鲜芽叶里的水分。
接下来的半个月,茶场周围的居民区,每天都飘散着炒茶的味道。出锅的成品和未出锅的半成品,散发出的茶香不一样,无数人家炒茶的不同香气重叠在一起,芬芳馥郁的比美酒还醉人,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,去看别人家炒茶。这个时节,也正是人们观摩、购买炒新茶的时机。大街小巷每隔不远,就有在路边支个煤炉,上面架口大铁锅的炒茶人。
按道理说,炒茶一般要用专属的锅。但是日常百姓谁家也不是整日整年炒茶,基本都是一年炒这么一次。所以炒茶的锅,往往都是头天晚上还在炉灶上炒肉丝。然后主人把炒菜的大铁锅按在溪头水里,狠劲刷净再泡半天,去异味就是了。茶炒得好不好,重点在于炒茶人对火候的掌握。
当煤炉的火烧热了铁锅的时候,炒茶人先抓一把芽叶扔进热锅里,接着翻动搅拌。这个搅拌的过程,不能用锅铲勺子甚至筷子等任何厨具,只能用手。一方面器具怕损伤了叶芽破坏了茶香,另一方面是不允许叶芽沾染上其他异味。一般的炒茶人,都是把手用清水洗净后,戴上个帆布手套。也有对茶叶的品质要求高的炒茶人,直接用手在热锅里翻炒茶叶。他那厚实带茧的手掌,将茶叶翻动几下后,把热锅里的茶叶抓起向上抛洒。为了使茶叶受热均匀,等茶叶纷纷落回锅里后,炒茶人再徒手从更加高温的锅底,重复抓起茶叶向上抛洒的动作。那种勇气,简直犹如油锅取栗般,不是一般人拥有。如此循环反复,直到茶叶散出炒茶人认为的,合适的香气变色成熟,出锅。炒茶人再将刚炒好的茶叶均匀摊在簸箕里。均匀摊开这点很重要,只有茶叶摊开均匀、冷却均匀,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:揉茶。揉茶顾名思义,就是用手揉搓,把已经充分均匀冷却的茶叶,在簸箕里,按照同一个方向,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方向,进行揉搓。揉搓到茶叶的形态和干燥后的茶叶一个样子的程度。炒茶人在揉茶时候的表情比炒茶时候的表情还要专注。也许是因为这一个步骤就是画龙最后的那道点睛。此时他略微斑白的两鬓,和低头明显凸出的酱色的腮骨,都因为认真而显出一种岁月的美感。这时,一直静默观看的,围在炒茶人附近的人们都长舒了一口气,仿佛一个大工程竣工,开始对着炒好的茶叶评头论足。炒茶人默不作声,淡定地把茶叶留在簸箕里,搁在通风干燥的地方,一般这样风干一两天,就可以把茶叶装罐子收藏了。
那次有幸,气温一直晴好。一天后,微风袅袅燕啾檐下,我端坐庭院,在江南最美的时光里,品到了亲手采摘的明前茶。
(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、辽宁省散文协会会员、辽宁省传记学会会员)